





Karina Smigla-Bobinski
ADA – ANALOG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File Festival
与Tinguely的“Méta-Matics”相似,是“ ADA”具有灵魂的艺术品。它自己行动。在丁格利(Tinguely),成为一个疲惫不堪的机械人就足够了。他费力地看了一下:这台机器除了工业上的自毁能力外什么都不生产。而Karina Smigla-Bobinski创作的《 ADA》是一种后工业的“生物”,是访客动画,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雕塑,自我形成的艺术品,类似于一种分子杂种,例如纳米生物技术中的一种。它开发了相同的旋转硅碳混合动力,小型工具以及能够生成简单结构的微型机器。 «ADA»是更大的,美学上更复杂的交互式艺术制作机器。充满氦气,自由漂浮在室内,透明的,类似膜的地球仪,掺有木炭,在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上留下痕迹。尽管访问者感动,但«ADA»产生的标记是非常自主的。地球获得了活泼的气氛和黑煤的痕迹,看上去像是一幅图画。地球仪开始行动,制造出由线和点组成的线条,无论其强度,表达方式如何,访客都难以控制“ ADA”以驱使她驯化她,这仍然是无法估量的。不管他尝试什么,他都会很快注意到,《 ADA》是一个独立的表演者,用图画和标志signs满原始的白墙。越来越复杂的织物结构出现。这是视觉上的动作,就像计算机一样,在输入命令后也会产生无法预料的输出。并非徒劳的《 ADA》让人想起Ada Lovelace,他在19世纪与Charles Babbage一起开发了第一台计算机原型。 Babbage提供了初步的计算机,Lovelace是第一个软件。数学与她的父亲拜伦勋爵的浪漫遗产共生于此。 Ada Lovelace打算制造一种机器,该机器能够像艺术家一样创作诗歌,音乐或图片之类的艺术品。 Karina Smigla-Bobinski的《 ADA》秉承了这一传统,同时也是Vannevar Bush的创始人,他于1930年建立了Memex Maschine(内存索引)(“我们希望Memex的行为像复杂的步道网一样通过大脑的细胞”或提花织机,为了编织花朵和叶子需要打孔卡;或Babbage的“分析机”提取算法模式。 «ADA»在当今生物技术领域兴起。她是至关重要的表演机器,随着观众参与人数的增加,线条和点的样式变得越来越复杂。留下艺术家和访客都无法解读的痕迹,更不用说«ADA»了。而且,“ ADA”的工作无疑是具有潜在的人性化的,因为对这些标志和图画唯一可用的解码方法是,我们的大脑在睡觉时最多只能联想到这种联系:梦tru以求的严峻爵士乐。 (由Arnd Wesemann撰写)

Tobias Putrih
A, H, O, I, ! …
在视觉艺术与建筑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上,托比亚斯·普特里赫(Tobias Putrih)的结构可以满足建筑程序的需求,可以代表艺术品本身,也可以作为其他作品的展示。参考文献的融合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他的作品都通过提及1960年代的建构主义项目和短暂建筑,或者通过与包含现代建筑的纯净几何结构的对比,唤起了20世纪对现代性的某种记忆。与电影及其设备的关系加强了这种空间实验,这是电影形式所指的同一现代性的重要里程碑。在露台上Putrih拥有无形的皮肤,其视频投影空间采用模块化的木材和纸板结构,其线条灵感来自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的Palácioda Alvorada的柱子。除了向巴西利亚致敬之外,艺术家还进行了遮盖过程,其中宫殿的清晰而灿烂的支撑点被复杂的皮肤覆盖,这些皮肤重申并抵制了整体的轻盈,使保护性皮肤成为对象沉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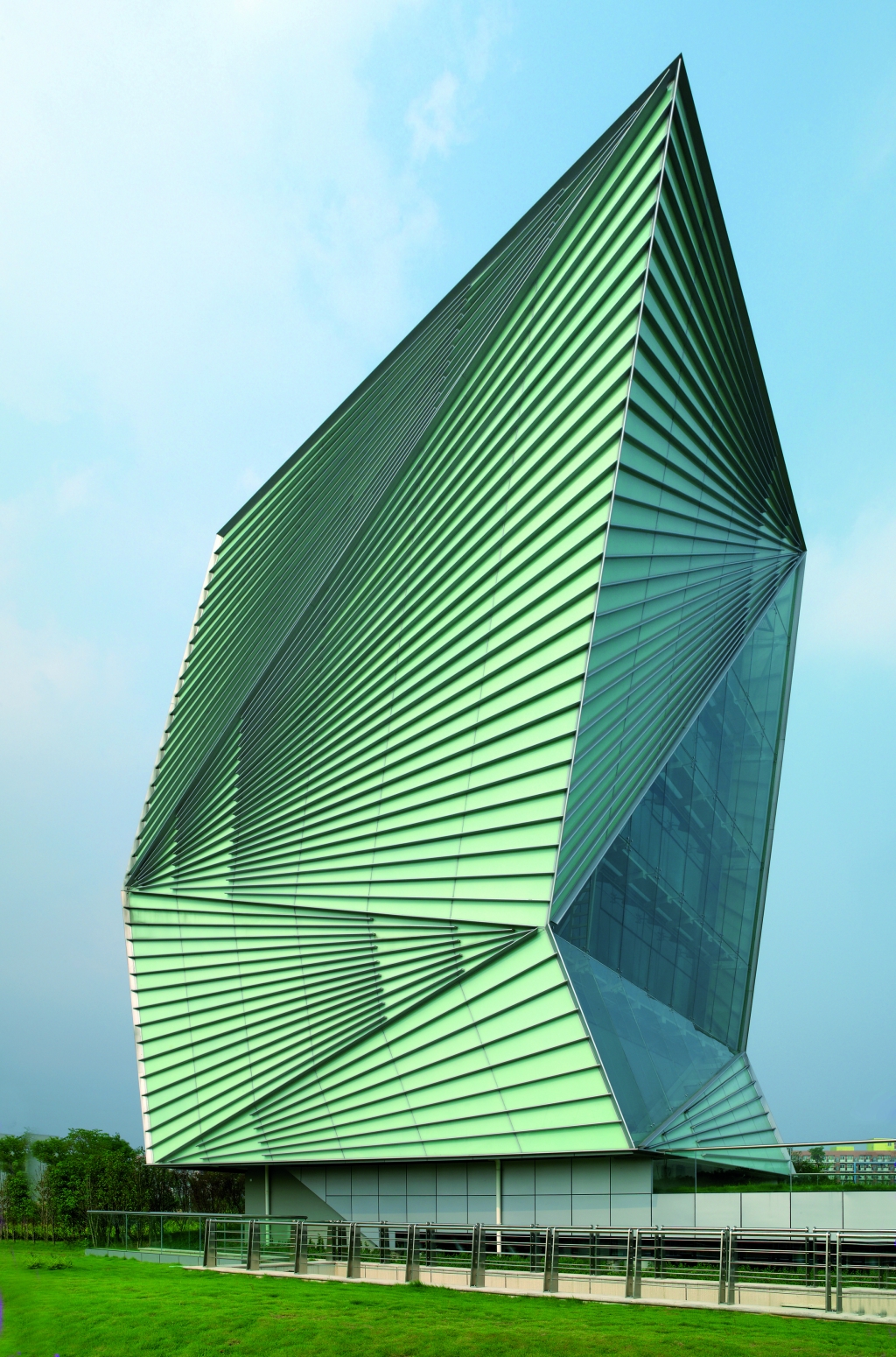
Mario Cucinella Architects

ERNESTO NETO
Эрнесто Нето
ارنستو نيتو
埃内斯托·内图
ארנסטו נטו
エルネスト·ネト
어 네스 토 네토
ErnestoNeto被认为是巴西当代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他的灵感部分来自于巴西现代实体主义(neo-concretism)。Neto创作的抽象装置常常占据整个展览空间。他所使用的材料非常的轻薄。弹性尼龙和棉常常被用到。比如优质的薄膜被拉长固定在天花板上,弹性的纤维挂起来形成一个房间,或者一个类似器官的形状。有时这些形状内填满了有气味的香料,挂起来后仿佛一滴眼泪的形状看起来又像是一个巨大的蘑菇或者是袜子。又有时他创作一些特殊结构的软体结构,参观者可以通过表面的小开口进入到里面。他还创作过一些类似迷宫的空间,参观者可以进入去体验它的作品,并与其产生互动。
Neto的艺术是一种体验,它们时而和人的身体发生关系,时而类似人体器官。他自己描述他的作品是一种从内部对身体景观的一种探索和表现。对于neto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参观者应该动起来亲自去和作品产生互动,通过身体接触,气味等去感受。

Martin Kersels
Olympus
“马丁·凯瑟斯(Martin Kersels)这种刻薄和非常规的语言起源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激进艺术形式,其特征是高低文化元素的混合,理论观念以及矫正和退化的材料。
这位艺术家于1960年出生于洛杉矶,他为都灵个展创作了一些机械雕塑,照片和素描,其灵感来自于地下文化中最具争议和颠覆性的偶像:伊吉普·波普(Iggy Pop),磁石摇晃的社会衰弱诠释者,著名为他的舞台表演。他的音乐简陋而病态,没有希望和乌托邦,却陷入decade废,灭亡和虚无主义。在“ Fat Iggy”项目中,Kersels解构了Iggy Pop图标,以阐述新的神话。
这位歌手所代表的肥胖身体的decade废使他从神话中重获新生,而在展览空间中心突出的钻石形象则与明星的轨迹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石头冰冷而不可触动的美丽源于它进入大地子宫的漫长而无声的旅程。与短暂的幽灵联系在一起的喧闹声中,只有碎片,破碎的镜子散落在房间周围,无法恢复和谐统一的形象。”
珍妮·多利亚尼(Jenny Dogliani)

Maiko Takeda
舞妓武田
武田舞妓
מאיקו טאקדה
마이코 다케다
مايكو تاكيدا
Shadow Jewelry
逻辑+几何+空间构成了武田舞子所有作品的共同点。在这个世界中,简单会显得复杂,秩序会变得混乱。但不要害怕沉迷,因为最后您将始终发现公分母站立着(就在它所属的底部)。
武田舞子(Maiko Takeda)在繁荣后的东京长大,在那里她很快面临着要在一个缓慢停滞的国家创造具有个性和永恒品质的产品的挑战。这意味着她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时尚和流行文化以外的地区,以步行的方式探索这座城市,从最小,最随意的事物中寻找灵感。
在作品中,各种元素并存。阴影,风和重力等环境影响为装饰带来了奇观和迷惑。她的作品本身绝不是唯一的形式,因为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多余的元素总是试图超越佩戴者的期望。


PRESTON SCOTT COHEN
Tel Aviv Museum of Art
Amir大楼的设计直接源于在狭窄,特质,三角形场地内提供几层大型中立矩形画廊的挑战。解决方案是通过在不同的轴上构建水平线来“对三角形进行平方”,这些水平线会在地板与地板之间有很大的偏差。从本质上讲,该建筑物的楼层(上两层,下三层)是结构上相互独立的平面图,一层一层地叠在另一层上。
这些高度通过“ Lightfall”统一起来:“ Lightfall”是一个87英尺高的螺旋形顶棚中庭,其形式是通过巧妙地扭曲曲面来确定的,这些曲面在建筑物中上下弯曲和转向。 Lightfall表面的复杂几何形状(双曲线抛物线)将画廊的不同角度连接在一起;沿着它们的楼梯和倾斜的长廊是令人惊讶的,不断展开的垂直循环系统。而来自上方的自然光则折射到半埋式建筑物的最深凹处。悬臂可容纳平面图之间的差异,并在周边提供悬挑。
这样,阿米尔大厦将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范型结合在一起:中性白盒子博物馆为艺术展览提供了最佳,灵活的空间,而奇观博物馆则使参观者感动并提供了非凡的体验。社会经验。阿米尔大厦(Amir Building)对原始几何形状和传统几何形状的综合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博物馆体验,这种体验植根于巴洛克风格,就像现代一样。
从概念上讲,阿米尔大厦与博物馆的野兽派主楼(于1971年建成;建筑师丹·艾坦和伊茨查克·雅沙尔)有关。同时,它也与特拉维夫现代建筑的更大传统有关,从孟德尔松,包豪斯和怀特城的多种词汇中可以看出。外立面闪闪发光的白色抛物线由465种不同形状的平板组成,这些平板由预制钢筋混凝土制成。立面实现了城市前所未有的形式和材料的结合,将特拉维夫现有的现代主义转化为当代和进步的建筑语言。

DMITRI OBERGFELL
Дмитри Обергфейла
infinite ladder
在他的实践中,Dmitri Obergfell有兴趣探索材料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以评论人类的经验。 由于观看者对制成品的熟悉程度以及与日常体验的关系,他将商业性制成品用作白话。
人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既是作品的访问点,又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联系的方式。 他希望观众有一种将他们暂时摆脱自我的体验,并让他们考虑更广泛的存在感,更多的社交或集体体验。 德米特里(Dmitri)被当代人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与历史的关系的看法和/或方法所启发。 他说:“我花了大量时间吸收信息并被动地观察周围的事物。 我认为我的灵感就像渗透。 我更喜欢保持不确定性,以免我的灵感变得陈腐而过时。’



TRICKY WALSH AND MISH MEIJERS
The Wasp Project
黄蜂工厂决定了伊恩·班克斯同名小说中小说的主人公,事物的命运。弗兰克(Frank)使用尖端中发现的残迹残骸创建了一个复杂的,昆虫特有的酷刑装置,以确定未来特定事件的结果。
在最初的Wasp项目中– W.A.S.P.寄生虫挤满了过时的机器,对齿轮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对忙碌的辛劳造成的影响视而不见。从远处看,它们像是在挖洞的“白蚁”慢慢地解构它们的宿主,近距离地看,它们是微型的城市化区域,强调了两个独立结构之间的规模差异-理性,实用的机器和无序,随机的鼠疫。
机器元素–受到2008年底巴黎艺术与博物馆(历来最受欢迎的灵感来源)的访问的启发。整个房间都布满织机和织布机,并面对着1700年代起的一台巨大的机械织机。它的“可读性”结构力学和优美的外形彻底地,几乎毁灭性地移动着。我主要受到建筑和机械的启发,它们的工作方式可以在视觉上“读取”并理解。这项工作似乎是我进行研究的转折点,从光学机器到使用眼睛以及将其用作机械化设备的方式,这都是我研究的转折点。

TIM HAWKINSON
蒂姆·霍金森
ティム·ホーキンソン
تيم هاوكينسون
蒂姆·霍金森(Tim Hawkinson)的作品有多种艺术形式,包括绘画,绘画,摄影,录像,装置和声音,但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雕塑。他以使用简单的方法,工具和零件制作复杂的结构而闻名。例如,用电工和塑料布制成的风笛大小相当于足球场的大小。这不是他唯一以音乐为特色的作品。还有他的作品《五旬节》。它的特征是在纸板树上竖立了十二个与自己一样大小的雕塑。这些都被编程为播放宗教赞美诗。他还以创造动感和发声元素的纪念性作品和微观作品而闻名。总而言之,他的作品既以科学为基础,也以艺术为基础,尤其是因为他经常为自己的作品创造新的发明和工具。
蒂姆·霍金森(Tim Hawkinson)的灵感来自他自己的身体,并试图对其进行重新想象。确实,有时甚至会牵涉到他的身体,例如当他使用自己的指甲剪和头发做雕塑时。他还喜欢表达生命,死亡和时间的流逝。


SHEN WEI
Шен Вей
שן וויי
沉伟
Folding
沉伟的作品“折叠”(图为公园大道军械库)于2002年在纽约首次上演
胸白,胸甲白,脸白,并带有细长的发卷(头饰?他们的头是细长的吗?),第一批舞者从黑暗中冒出来,紧a在蓝绿色的阴暗地板上,拖着长裙摆,这些长裙摆的颜色各不相同。将它们分为两组:红色和黑色。红军们经常在国会中扮演举动,旋转,独立的生物,而黑军人则用布成双成对地密封在一起(例如令人毛骨悚然,悲惨地交织在一起的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的作品),并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极其缓慢的性交活动。甚至是较慢的葬礼游行,将他们死气沉沉的双胞胎恋人拖走了。
看来,红军有个国王,而黑人则有一个皇后(最终他们一个人出现)。后来的动向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当红军发现团结一致时,讽刺的是,他们似乎拒绝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沉伟的王者角色,同样如此),而成对的黑人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开明的人。他们的配对斗争中的个性。另外,这标志着我第一次看到全身氨纶套装,它的穿着者是真人版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一个动员的浮雕,出现在背景中像是一些小故障。在这个二项式世界的软件中。也许这个不露面的角色是红色和黑色的合成,或者是崇拜者的至高无上的梦想,将两个部分折叠成一个整体。也许这个角色只是个次要角色,但是因为它脱颖而出,它具有波巴·费特的所有明星般的特质,并且陪伴着我进入了第二次中场休息。
最后的作品《未分割的分裂》上周在军械库中获得了世界首屈一指。舞蹈首先是近距离偷窥的一种练习。次要的是它关注性的各种表达方式-觉醒,压抑的范围,自由,偏见,模式和失败。我和其他人一起在网格上的60个单独的瓷砖上漫游,我的第一个想法(以及其他所有人)是我的上帝,舞者拥有地球上最不真实,雕刻最精美的尸体。我永远不会再发生性行为,直到我看起来像那样或与那个样子的人在一起。
我看过大约五十种以裸体为特征的舞蹈,几乎每次都在推动正式的脱敏或去性行为,有时是由编舞者或舞蹈家发起的,但主要是由我自己做出的,以便让我看到过去的裸体并与之交往。在不同级别上具有更高灵敏度的性能。这通常需要大约20秒钟的时间,然后舞蹈的表现力和运动学所伴随的抽象在一定程度上使身体脱性别-我认为这不是脱胶过程,而是更接近于暂时的集体异化。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面对着滑稽表演的现代舞蹈表演,尽管观众之间的距离已定,但仍邀请观众保持性意识。这发生在未分割的分割中。

SCOTT SNIBBE
Deep Walls
《 Deep Walls》是投影的电影回忆内阁。当一个人走进其投影光束时,交互式墙开始记录他的阴影以及跟随者的阴影。当最后一个人离开框架时,阴影在十六个矩形小橱柜中的一个内无限重播。与结构主义电影一样,重复性视频的收集成为其自身的对象,而不是严格地具有代表性的“电影”。 “深墙”在电影循环之间创建了复杂的时间关系。每个小阴影胶片都有精确的记录持续时间:从几秒钟到几小时。 16帧之间的时间关系变得复杂(以类似于Brian Eno的磁带循环实验的方式),将不同持续时间的单个记录循环播放,以创建连续几天都不重复的构图。 Deep Walls的灵感来自Jan Svankmajer和Quay Brothers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以及Joseph Cornell的雕塑。在他们的电影和雕塑中,小尸体和强迫性地收藏在橱柜和抽屉中的物品代表着心理和精神状态。组织的理性过程带来了一种无意识的非理性。 Deep Walls的名称受到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图案语言”(Pattern Language)设计图案的启发。他建议建造厚厚的房屋墙壁,以便居民自己可以雕刻出橱柜,抽屉和窗户来个性化房屋。本着亚历山大的精神,这部作品逐渐记住了其表面上的环境内容。

VICTORINE MÜLLER
维克托里娜米勒
维克托琳·穆勒(VictorineMüller)以巨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PVC充气动物和其他有机形式的充气雕塑而闻名,但其真正的魔力始于这位瑞士艺术家本人的存在。 Müller经常打扮这些空灵而又不同的灵魂,在某种精神上的表演中将它们揭示出来,声音和图像被结合在一起,吸引着沉思的听众。这位艺术家和平地生活在透明而有光泽的生物中,使人们与她和她的水晶雕塑建立了非常亲密的联系。
“我对创造敏感时刻,我们的防御能力低下以及我们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的时刻感兴趣。 (…)我创建区域,呈现图像,显示触摸观众的过程,调用各个级别的关联并将它们传递到不同的状态,以便隐藏的事物变得可见,可访问,开放的可能性-展示它所能展示的东西不是说,不能说,但是是。”